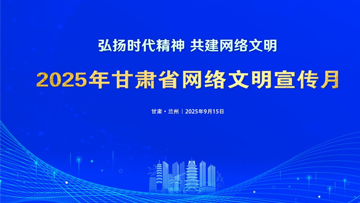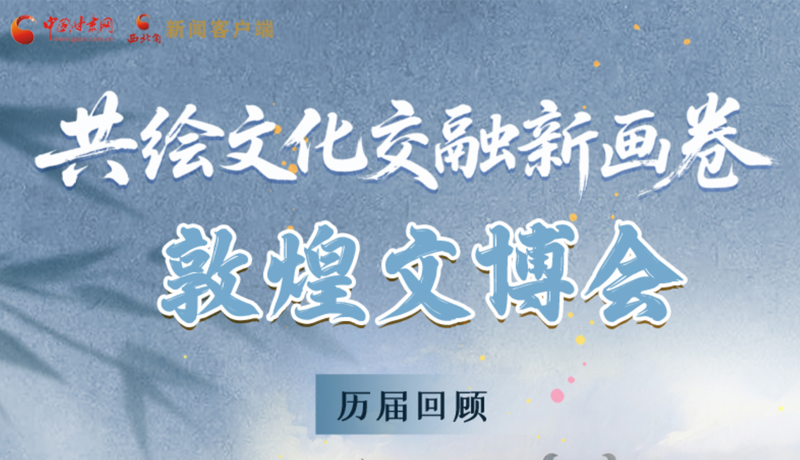■ 張家鴻
訪談錄,是人與人精神交流的直接形式。訪談的有始有終、訪談的可持續推進,源于或多或少的共鳴。不求全然一致,更不能故意唱反調。由眾人提問、陳子善作答的訪談錄《文學現場的真實與想象》,正是同理心與共情力的載體。
初品此書,涌上心頭的第一個詞,竟是瑣碎。受訪者陳子善是瑣碎的主體。但在我看來,瑣碎這個詞并無貶低作者之意,恰恰相反,它有其特殊的風格和價值。試問:若不瑣碎,文學現場的創設從何而來?現場之真實,憑依于何物?陳子善是如何從事文學研究的?他如何找到新的興奮點與起點?他怎樣找到那么多珍貴史料?他如何看待因各種原因被湮沒于歷史的文化人與學者?
在這本書中,瑣碎的內容既指向文學的真實,同樣指向訪談這一交流方式的真實。訪談是人與人交流的現場,一個提問,一個回答,語氣、語速、表情、提問或回答的長與短,都關系著對方的回答。瑣碎帶來真實,真實源于瑣碎。這與陳子善注重史料的學術研究是一樣的。
對他來講,最重要的轉折點莫過于1976年參加1981版《魯迅全集》注釋工作。“因為我參加注釋的部分是魯迅1934年到1936年寫給朋友、學生的書信,這些書信往往是很具體的,涉及具體的一件事情、具體的一本書、具體的一句話,那么按照注釋的要求我們都要注明出處,注明來歷,比如魯迅為什么會在信當中發這段議論,都要查清楚,所以逼得我不得不去做這樣比較仔細的查找的工作。”可以想見,在與學生、朋友的書信往返中,魯迅必然提及諸多文學外的生活中的瑣事。錙銖必較的態度對史料的真假、有無而言,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在這本書中,文學現場不止于一處。因為陳子善的深入研究,所以有現代文學發生的第一現場;因為有陳子善一生不斷的書緣,所以有他熱愛閱讀文學作品與深入研究現代文學的第二現場;因為有陳子善接受不同提問者的采訪,表達關于文學與諸多現代作家的觀點,所以有第三現場。
首先,它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諸多事件發生的現場。直至1934年5月黎烈文離開《申報》為止,魯迅在該報副刊《自由談》發表雜文超過100篇,這與郁達夫居中介紹有關。郁達夫與魯迅交情匪淺,黎烈文又很尊重魯迅,故而魯迅答應得爽快,寫得也很投入。如此,才有現代文學史上諸多雜文佳作。
其次,它是身為學者的陳子善尋找、梳理、考證、品鑒、總結史料的現場,往往是他一人獨處。中華書局遷往北京之后,有報刊雜志留下交給《辭海》編輯部。為進入資料室查詢,他費了些心思才得以實現。“于是,我就在里面爬上爬下查閱舊報刊,渾身上下弄得都是灰,但心里是高興的。那段日子里,每翻開一份報紙,在副刊上看到一篇我不知道的或者此前沒有文獻研究記載的我所關心的作家的作品,那種喜悅至今都難以忘記。”那是學術研究的起點,雖然苦累,卻甘之如飴。后來,乃至后來的后來,這樣的情景是陳子善的家常便飯。有段時間,陳子善經常到柯靈家中請教。下午三四點鐘去,五六點鐘離開。談論一兩個小時,主要是為人客氣的柯靈講,講創作歷程文壇往事,陳子善聽,聽得很用心。從夫子游,是極好的學習機會,可遇不可求。
第三,是陳子善與沈嘉祿、陳佳勇、王賀、張德強等人交流中國現代文學的訪談現場。誠如李浴洋在《總序》中所說:“道理的闡發、觀點的碰撞,為的是達成更為全面與有效的認識;思想的對話、靈魂的共振,為的是形成更具洞見與理性的價值。人與人的精神交流可以不必劍走偏鋒,但要有共同的底線,也可以鮮明秉持自家立場,只是不宜喪失同理心與共情力。”把提問者與受訪者定位為文學的知音,是不會錯的。否則,何來提問的動機?哪來回答的意愿?
從第一到第二直至第三文學現場的更新換代,是可貴且美好的傳承。對陳子善來講,是貫穿他閱讀史與成長史的重要線索。為何陳子善會退而不休?因為熱愛或癡迷不隨退休而終止,其長度甚至可以說大體與生命等同。《文學現場的真實與想象》的訪談完成于不同時間,談的是彼此有關聯又有所側重的話題。由今視昔,可看出一位學者行走與成長的軌跡。故而,這本書也可以說是一本特別的回憶錄、成長記。
- 2025-09-22五位戰地攝影師的抗戰紀實——讀《追光者》
- 2025-09-22滹沱河畔梨花香
- 2025-09-22拿起筆,人人都來描繪“生活本來的樣子”——素人寫作大家談
- 2025-09-17北京之秋遇書香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