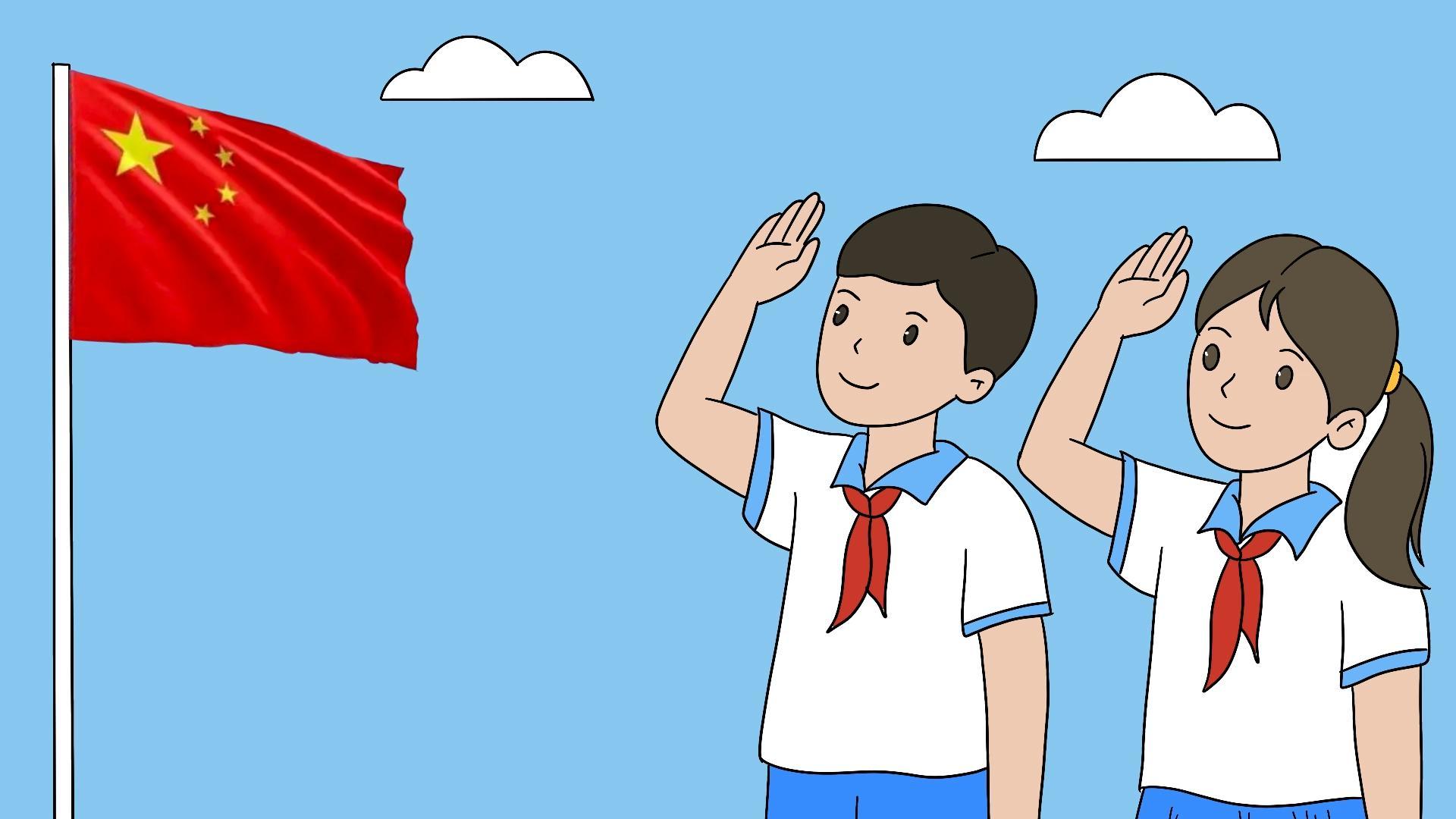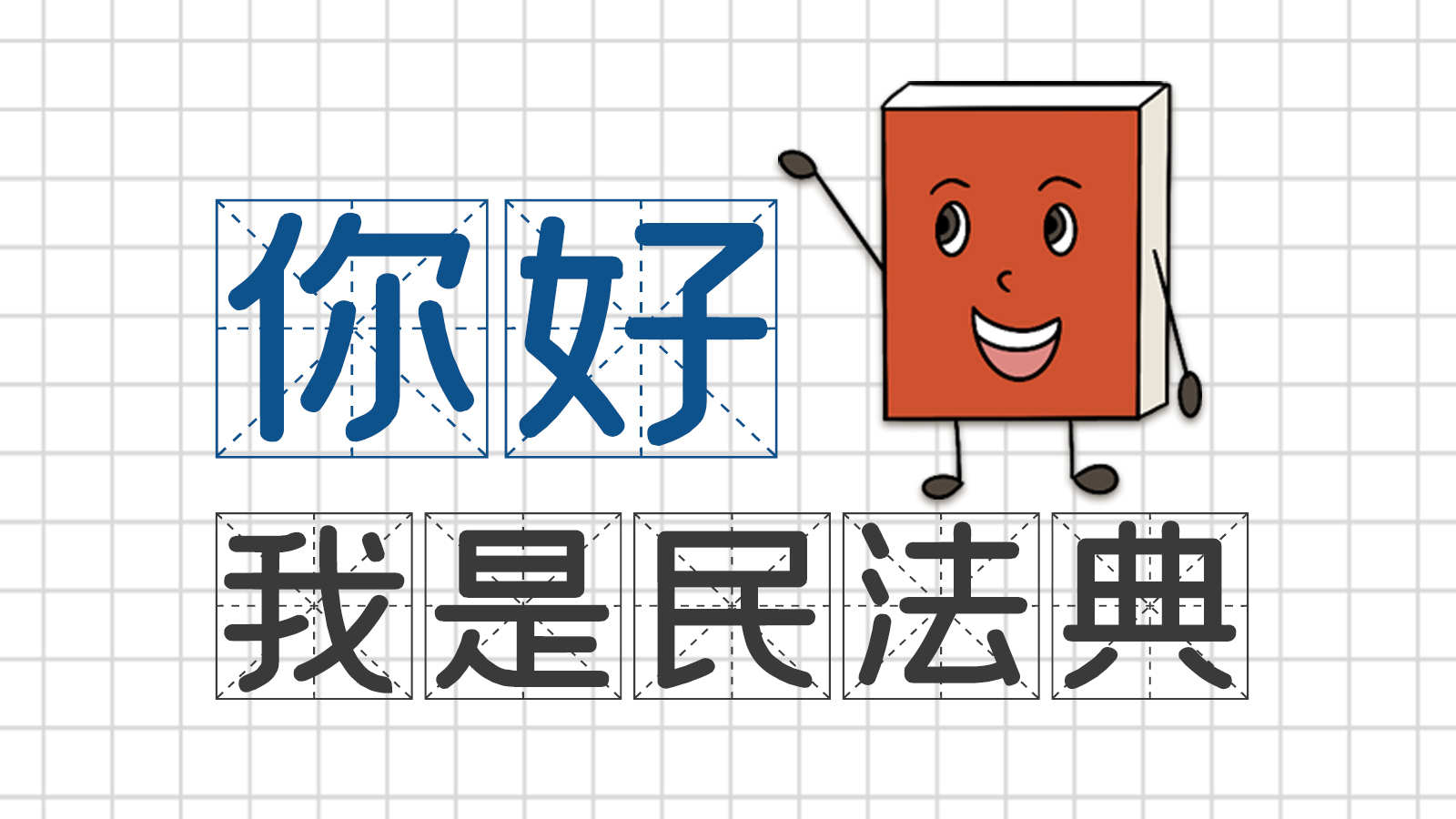趙元文
秋天的草原有秋天的況味——遼闊、明凈、成熟、豁達,甚或有點寂寥。整個草原呈現出一派青黃不接的景象,牛羊沒入其中,像一堆堆石頭,寂然無聲。一些小河邊或者濕潤的地方,仍舊開放著一些細碎的花朵。比如掩藏在草叢中的藍瑩瑩的羊卓花,還有一些米黃色、紫紅色的叫不上名來的小野花……天空偶有幾只滑翔的鷹,不時發出一兩聲尖銳的鳴叫。遠處小山頭上的經幡,五顏六色,隨風飄舞。這天蒼蒼、野茫茫的草原秋景,突然會令人沉靜下來,會令人失去一切浮躁的意緒,引導你復雜的心態、功利的欲念頓然消失殆盡。《綠地》雜志編輯秋靜就是在這個時候來訪的。她曾說過要來海北看看草原的,但沒想到來得如此之快。她是貴州人,大大咧咧,說起話來倒豆子一樣,不管你聽不聽,她都那樣。當她發覺你沒聽她說話,她會仰起頭來哈哈大笑,然后說:“你云游呢?真不夠哥們兒!”接著吸兩口香煙,再吐出去。秋靜既然都來了,那我就得安排她去看草原。眼下真是一個秋高氣爽的好季節。這時,我突然想起了索南才讓——海晏縣托勒鄉德州村的一位牧民。想起他是因為他在學寫小說。
那是6月的一天,我收到一篇州中學一位學生從郵局寄來的稿件。信封像一個檔案袋,里面厚厚的。拆開一看是一篇叫《沉溺》的小說,署名董澤文。拿回家看完后,覺得有點靈性,改改,也可以發。隨后,我按信封上的地址,聯系到班主任,讓她查查這個學生。結果小說不是這個學生寫的,是他的哥哥寫的,他哥哥在德州放羊,來不了,讓他帶到州上寄給編輯部的,我隨之給這個學生捎話,讓他哥哥來一趟編輯部。一個禮拜過去了,也不見人影。過了近半個月,我還惦記著這事兒,但這個署名董澤文的作者,還沒有從草原深處走出來。按理說德州村距州上并不遠,就29公里。有一天下午,剛上班不久,一位小伙子走進了我的辦公室。他穿著一身合體的黑西裝,個頭在一米六左右,很精瘦、很精干,發型有點像流行歌手,很時尚,看上去二十出頭的樣子。我說:“你坐,有事兒嗎?”他說:“《金銀灘》編輯部的老師捎話讓我來一趟。”噢,我突然想起來了,“你是董澤文?”他說:“是。我在牧場放羊,那里沒有信號,也不通電話。前兩天,弟弟才捎話來。”在與他的閑聊中,知道他生于1985年,是蒙古族,叫索南才讓,漢名叫董澤文,小學四年級(12歲)輟學放牧至今,但從外貌上一點也看不出牧民的影子。他說以前寫詩,但沒有感覺,就不寫了,后來在州上的一家書店看到了《金銀灘》雜志,便買回家閱讀,再后來那家書店不開了,《金銀灘》也買不上了。閑聊一會兒后,我對索南才讓談起了小說《沉溺》的看法以及修改意見:“小說很有草原的生活氣息,也有幾分靈性。整體寓意明朗,意境很好。干什么事都得有一個良好的心態,否則,欲速則不達。主人公才郎就是一個例子。”“小說的結構有些亂,要調整,倒裝句太多,讀起來不流暢,要改……”后來想想,他在草原深處,一來一往又得耽擱好多時日,干脆我修改得了。索南才讓一臉感謝。最終,這篇小說發表在《金銀灘》2006年第4期上。一位云南作家讀完這篇小說后說:“一個只有小學文化的牧民寫得不錯,有點靈性,以后有空來青海一定見見他。”
秋靜的到來,使我突然想到了索南才讓和德州村。德州村有一處德州墓地,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因為在德州墓地內發現了銅鏡、陶片、錮簇,是卡約文化的發源地。況且,我一直想看看索南才讓的生活狀況,便脫口而出:“我們去德州,看看一位作者。”秋靜說:“隨你的便,我只管跟你走。”我拿上《金銀灘》雜志,讓徐師傅送我們去德州。
正值早上10點,沿途的空闊、沉靜使秋靜激動不已。草原半坡上牧民的房屋大多單院獨戶,煙囪里冒出的濃煙彌漫著牛糞的味道,遠遠會聞到酥油和奶茶的香味,那韻味像一幅歐洲油畫。秋靜很激動地說:“我煩惱時或者老了以后就在你們草原上買間房子住下來,多安靜、多詩意、多有情趣啊!到那時,我會邀來很多知心朋友來這里享受人間的美景、享受生命、享受生活。”我側頭看看窗外,那一群群黑白分明的牛羊群散落在秋天豁達的草原上,靜謐極了。想想秋靜剛才說的話,也真有人間童話的寓意。文人大多愛幻想,喜歡追求一種性情的生活方式,但一些沒修養的人罵人總會說,你咋跟文人一樣。而這類人總喜歡厚著臉皮拍馬溜須,阿諛奉承。他們待人總會帶著功利的目的,十足的變色龍,不懂得人間的真誠情懷。文人追求性情的天性,是他們對生活充滿了理想主義的幻想所決定的。一個作家、藝術家總是要表達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眼光、角度對世界作出自己的認識和解釋,從而影響他人。
在與秋靜閑聊當中,就到了德州村。我下車到馬路邊一家寫著“德州小賣部”的小店里去打問索南才讓的家。一位穿著藏袍的老阿奶用生硬的漢話說:“我們這里沒有這個人。”我費了半天的口舌,把雜志拿出來讓她看,說明來意后,她說:“你說的是董軍,是我的侄兒。他到山那邊的秋季牧場擋羊去了。”
我們又在老阿奶的指點下,拐向通往草原深處的一條簡易沙路。我想起魯迅的名言: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眼下的這條路就是“走的人多了”之后變成的路。從路的狀況來看,除了經常行走的手扶拖拉機、摩托車的轍印,就是馬蹄印。兩道深深的車轍使路中間凸顯出一道高高的土坎。奇瑞轎車行走起來很艱難,這位老家北京的徐師傅總會把車的輪子擱在中間凸起的土坎和深轍的邊沿上行走,他說,這算什么,當年他在地質隊開車,那路就沒個路形兒,不打緊,慢慢走吧。
我們一邊在土道上顛來蕩去,一邊觀看著草原的美景,無垠的藍天一塵不染,陰濕的地方仍舊開放著一片片碎小的野花。翻過兩個山梁后,終于俯瞰到一望無垠的牧場了,白色的帳篷點綴著草原,牛羊馬匹到處皆是。路上碰上幾個騎摩托車到州上或縣上去的牧民,他們指了指索南才讓家的帳篷。因為隔一道小溝,車無法行走,便讓徐師傅等著,我和秋靜朝那頂白色帳房走去。草原上的路看起來很近,但走起來會跑死馬。各家離得很遠,各色藏狗高大魁梧,被鐵鏈牢牢地拴在帳篷邊,見到陌生人后,渾厚的吠聲就會帶來一片叫聲,一群群百靈鳥飛起來又落下。許是長期沒有外來人的緣故,藏狗一叫,牧民就走出各自的帳篷看看,不說話,只是盯著你看。
快到索南才讓家帳篷前時,遠遠地走來了一位中年男人。他一邊躬著腰,一邊伸出雙手,掌心向上表示對我們的尊敬和歡迎,草原牧民都是這樣憨厚、直爽、不存介心。他說:“一天沒事做,那邊有小賣部、臺球桌,看他們搗臺球。”他一邊說一邊打開帳篷的門,我們坐在他的床邊。他要生爐子、煮奶茶,被我們拒絕了。因是臨時放牧點,屋內很簡陋。我看見一臺12寸的黑白電視機,一臺靠太陽能發電的機子,機子帶有VCD、收音機、照明等功能。我說:“我們來看看董澤文。”他說,他不認識,我說就是索南才讓,他也說不認識。我有點懷疑是不是搞錯了。我把雜志遞到他手上說:“里面有董澤文寫的文章,他是不是上小學四年級就不念書了。”這位中年男人說:“我不認字。我兒子念了個小學四年級,沒錢供他,就擋羊了。”我突然對他說:“就是董軍。”他說:“呀呀,董軍,我兒子。他到冬季牧場去了,我們的家就在冬季牧場。”隨后,我們走出索南才讓家的白色帳篷。他說:“天氣冷了,我們再有一個月就回德州去,我家里有五間土房,你們來噢!”臨別時,我說:“讓董軍好好寫,寫完就給我送來。”中年男人說:“他一直在寫。”
這遼闊的草原一望無際,秋靜真的不想走,她看到這撒滿草原的帳篷、牛羊馬匹、吠叫的藏狗、鳴唱的百靈鳥、嘩響的經幡,一下坐在茂盛的牧草上說,不走了,不走了。多美的草原啊,真像屠格涅夫筆下的田園牧場風俗畫!她左轉右轉地用數碼相機拍攝著風光。
秋靜無奈地隨我離開了秋季牧場,離開了德州村。遺憾的是沒目睹到德州古墓群,沒見到索南才讓這位蒙古族尕小伙。
她說,有機會她還來……
11月2日,當我從湖南參加完一個文學筆會回到單位后,辦公桌上放了一大堆來稿。其中就有索南才讓寄來的一篇文章。他在來信中說:
原上草先生:
您好,您送來的《金銀灘》已收到,謝謝。我很抱歉,讓您白跑一趟。日后,您若有時間請到寒舍一敘。雖然家中貧寒,但一杯熱茶總還是有的。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印在《金銀灘》上,我很高興。您知道當一個優秀的作家是我最大的理想,也一直努力向這個目標奮斗。這幾年,無論有多少困難我都沒有動搖過。在《金銀灘》上看到自己作品那一刻,我對自己說,你要記住這個日子,因為它標志著你已經開始上路了。從此無論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你都要堅決把這條路走到底。我真的非常感謝您給我這樣一個“表現”自己的機會。也許您會說這沒什么,但我還是要感謝您,感謝《金銀灘》。畢竟是你們給了我更大的勇氣和鼓勵……
索南才讓敬上
2006年10月31日晚
讀完索南才讓的信,我很感動。這使我看到了新一代青年牧民的內心追求。其實,生命就是一場充滿意外的偉大歷險,看上去難以掌握,其實機會無處不在。如果你從不犯錯,或者從沒有人批評過你,那么你肯定沒有進行過任何大膽的嘗試。如果一個人這樣生活,那么他肯定無法發揮出所有潛力,當然也就很難真心享受到生活的樂趣。人的思想和情感都應該像流水那樣自然,不要太刻意地去做什么、去追求什么。我很欣賞這句話:“人往高處走,高處不勝寒。水往低處流,低處納百川。”這是一種做人的境界。
我總認為:“一切生命都像塵土一樣很卑微。他們的身影出現在我的視線里,他們的精神沉淀在我的心靈里。他們常常讓我感覺到這個平凡的世界是那么的可愛,這個清淡的世界其實是那么默契,而看起來如草芥一樣的生命種子,其實是那么堅韌和美麗。”不管這是誰說的話,都將使我們所有卑微的生命擁有了重量和質量。
編后記
11月20日,由中國作家協會、北京市委宣傳部、湖南省委宣傳部主辦的“中國文學盛典·魯迅文學獎之夜”在北京中央歌劇院舉行,來自青海省海晏縣甘子河鄉德州村的蒙古族青年作家索南才讓,憑借中篇小說《荒原上》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他也是青海省首位獲得魯迅文學獎的作家。
在頒獎現場,索南才讓動情講起一位“放羊娃”發表第一篇作品的往事,并向觀眾展示當年的手稿,回憶了時任《金銀灘》雜志編輯趙元文老師如何到草原深處尋找他并帶他走上文學之路……本報編者通過索南才讓聯系到趙元文老師,特刊趙老師的這篇散文,也向編輯這一幕后耕耘者群體致敬。
- 2022-11-28天底下最甜的事
- 2022-12-02于制茶技藝中品味中國文化——“中國傳統制茶技藝及其相關習俗”緣何能成功申遺
- 2022-12-02在書的世界里,與溫暖相遇
- 2022-12-01在旅行中上一堂“生死課”,活在當下對抗虛無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